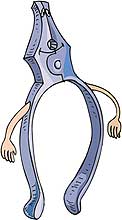
编者按:在很多情形下,爱其实是最难以表达的。因为爱,爱显得格外的曲折而深沉,也因为爱,才使得爱最感人至深。休 闲 宝 贝 网
1998年9月我带了个一年级班,担任班主任兼教语文、数学课,直到2001年10月我到上海参加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为止,前后3年多。一千多个日子,我每天和我亲切地呼之为“闺女”“儿子”的孩子们融在一起,上课一起学,下课一起玩,天凉了叮嘱他们多加衣服,天热了教给他们怎样去避暑……40多个孩子啊,我看着每一个孩子,感受着每一个孩子,—他们真正是我眼看着长起来的……
与孩子们的故事感动着他们的家长,感动着我的先生,也感动着学校的领导。为了我能够顺利地去上海进修,也为了班级的平稳过渡,2001年9月学校安排了安老师,负责教授数学课,随堂听我的语文课。为了让孩子和家长放心,学校承诺安老师只是临时代课,我回来后还教这个班。
得知我要到上海进修,孩子、家长舍不得让我走。因为我从未对孩子们发过火,孩子们和我的感情很深啊!因为他们从进这个班的时候就知道:这是个大家庭,老师就是妈妈,同学就是兄弟姐妹,大家要彼此真诚、关心帮助、团结友爱。但决定是不能改变的,并且有承诺在先,孩子和家长还是在依依不舍之中送走了我。四年级的孩子了,他们已经懂得感情、懂得牵挂。我在上海的日子里,每每接到他们打来的电话,就好像接到我亲生儿女打来的一样让我欢喜让我忧。
转眼3个月的学习过去了,我满载收获返回学校,已经是离2002年寒假不远的日子了。但一见面校长即平静地告知我:四年级要接受全县统考,安老师和孩子们合作得很好,这段时间尽量不要到班上去,以免分散孩子精力;先在家里休息两天,然后到校准备六年级数学教学,并且附言“必须得去”。
我心怅然!
殊不知,孩子们时时刻刻盼望着我早日归来。我到家后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就是他们打来的,他们嘘寒问暖,并询问我上班的具体时间。我听出了那小小的心的渴望。
当得知我要在家休息两天时,孩子们三三两两地来到家里和我见面,带来班里的消息:某某惹安老师生气啦,某某想我哭几回啦,某某睡觉梦见我啦……我一边和孩子们笑着,闹着,一边在心里嘀咕:该怎么和孩子们说呢?我在心里一直压着,压着……
上班了,整整一个上午,我一直留在校长室里,汇报我的收获、想法,聆听校长和县教育局领导的教诲。连喝水的机会都没有,更没有和孩子们见面的时间。
下午上班,我多想去看看班上的孩子们,但我强拉住自己的双腿,一直来到办公室。与教师们寒喧起来,上课铃响了,大家上课的上课,备课的备课,我只得和邻座的老师低声私语,但我的心很紧张。
突然,校长叫我到校长室。一进门只见安老师正在那里呜咽着说不出话来,校长严肃地陈述了事情的利害,要求我尽快稳定孩子们的心绪,保证孩子们在这次全县期末统考中考出好成绩。
我随即和抽泣不已的安老师到教室去。短短一分多钟的路程,我的思绪很乱。我的心经历了一种油煎般的痛楚。这种痛楚让我颤栗。
“就这样办吧!”我给自己打着气。我没有和安老师讲一句话。推开那扇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门,一股热情扑面而来,孩子们热切的眼睛、激动的脸庞、热烈的掌声和各色的气球、彩带、拉花以及黑板上红心黄框的“热烈欢迎柴老师回家”的几个大字……使我眩晕,几乎要把我推倒。
我沉着脸,眼睛看向地面,忍住不看孩子们,声音低沉着说:“同学们,我感谢大家。但是……”话没有说完,我转过身去,拿起板擦,奋力擦着黑板上的字迹,奋力撕扯黑板上方两侧各色的、大小的气球、彩带……
泪水早已喷涌而出,顺着我的脸颊流下……
我奔出了教室,不知怎样下的楼梯,在一楼那个没有人的教室里“呜呜呜”地哭起来……
过了好一会儿,我担心下课的师生会注意到我,和校长连招呼也没打,擦去泪水,踉跄着回家了……
第二天一大早,为掩饰红肿的眼睛,我换上了搁置好久的变色近视镜,来到学校,我径直走进了教室。孩子们都躲我老远。我的心在滴血啊!
我用力求平静的声音对孩子们说:“同学们,这段时间我负责咱们班的纪律,安老师负责授课。两个星期后全县统考,拿出你们所有的精力用来复习,争取最好的成绩;如果谁在全县统考考不好,我一辈子都不搭理他!”
此后的两周里,我每天早上、中午都要到班上坐一会儿,虽然不能与他们亲近,但能看着自己一手拉扯起来的孩子个个认真学习。这对我算是一点点安慰。不久成绩出来了,全县统考班级成绩第一,有四个孩子考进了全县前十名,皆大欢喜啊!但孩子们还是远远地躲着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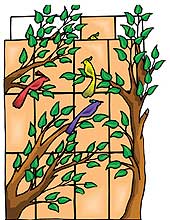
不久接到了孩子们的来信,我开始遭到他们的质问。心中真如翻倒了五味瓶。我对安老师说:“我临走那天和孩子们一起录的那节课,孩子们还没看过,他们提出来想看一看,我想明天下午让孩子们到我家去看,行吗?”安老师答应得很爽快。
回到家里,我马上准备,尽管家里已经有了苹果、梨、橘子、香蕉,但我依然到街上买来了西瓜、草莓、葡萄、小西红柿等水果,花生、瓜子、栗子、炒黄豆等干果,还有各种饮料。6岁的女儿见我忙得不亦乐乎,也帮我将洗过的水果分盘,端送。
一切收拾停当,先生出去了。孩子们来了,我高兴地去开门,全班41个孩子都到齐了。大部分孩子的表情已经缓和了,但仍然有9个孩子进门时只冷冷地看了我一眼,没说话。我知道:我真的刺疼了他们,伤害了他们。这是怎样的一种伤害啊?!
孩子们谁也不吃东西,也不喝饮料。以往不是这样的。女儿看到这种情况,有意和他们逗笑起来,使劲儿往孩子们的嘴里塞水果、塞花生,尴尬的气氛有了好转。
开始看录像了。沙发上、椅子上、板凳上,有的干脆席地而坐,但屋里一片寂静,没有了往常那种看录像时的玩笑。
过一会儿,有孩子啜泣起来。开始是1个,接着3个,5个,一大半的孩子都流泪了,有的孩子看着屏幕上回答问题的自己居然哭出了声。
我也早已泪流满面。
我关了录像,对孩子们说:“同学们,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有个女同学,我们俩是同桌,和我关系非常要好。她的妈妈很疼爱她。可是在她8岁那年她妈妈得了癌症,医生说还有6个月的生命。于是一家人都愁起来,她也担心妈妈的病……”
我顿了一下,孩子们都巴望着我。
“可是突然有一天,妈妈又得了一种怪病,那就是每天都要打她,不打不行,开始是用手打,后来用棍子,我的同学每天都跟我哭,说她的妈妈又如何如何打她了,她恨她妈妈。她妈妈必须每天打她一顿,要是她跑了,晚上回家时她爸爸、奶奶也要把她拉到妈妈跟前让妈妈打……”
我注意到了孩子们脸上的痛苦和疑惑的表情。
“我看着同学身上的伤痕只能和她一起哭,没有别的办法。后来,妈妈打不动她了就开始拧她,真正是拧得青一块紫一块的,特别是胳膊上,我不小心碰一下,她都要疼得叫起来。再后来,妈妈连拧她的力气都没有了,就用一把钳子来拧她,同学的腿上都是她妈妈用钳子拧过的伤痕。”
有的孩子尖叫起来了。
“这时候,我的同学不再跑了,她恨死了她妈妈。在我的同学忍受的非人的痛苦中,她的妈妈去世了,只活了三个月。”
这时,孩子们都哭了。
我接着讲:“在妈妈死后不久,一位新妈妈进门了,女同学和新妈妈的关系非常好,她特别知足,并且经常说:‘她倒不打我了呀。她不打我比什么都强。’时间过得很快,我的女同学22岁了,她该结婚了。在她结婚前的那天,我去了,她家里来了很多的客人,大家都很高兴。……”
孩子们开始议论起来。
“晚上,客人散去了,她爸爸给了她一封信,看完信她大哭起来。原来,那是她的亲妈妈留给她的信。信里,妈妈请求她的谅解,打她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她恨亲妈妈、忘记亲妈妈,能够和新妈妈和睦地相处。”
孩子们的眼里噙着泪水,但情绪已经平静了许多。
停了一会儿,我接着讲:“妈妈爱孩子,但是有很多的时候爱是无能为力的。正如我爱你们,也一样,如果当时我好好待你们,你们的心都在我这里,我又不能领着你们复习,上课时你们的心里都长了草一样,肯定考不出这么好的成绩。为了你们好,我只有狠心地一下扑灭你们对我的热情。”
很多孩子都点头了。我松了口气。
为了给孩子们一点时间调整情绪,我接着放录像。
看完录像,我又一次和孩子们谈话:“宝贝儿们,”我故意用轻松的语调说,“宝贝儿们,看看大家的心理承受能力怎么样?咱们来讨论一件事,如果下学期我不教你们了,怎么办?”
……
好一会儿的沉默后,我说话了。
“安老师为咱们班花费了不少心血,我们大家都应该尊重她,”回想起我在上海孩子们给我打电话时说过的话,我接着说,“也许安老师有这样那样你们看不惯的地方,或者说是毛病,我觉得咱们应该包容,或者说是真心地给她提出来,善意地给她提出来,就像你们包容我、给我提意见时一样,好不好?”
还是沉默。
“既然我不再教你们了,那咱们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相处了,咱们那样相处会让安老师心里难受,让安老师伤心的,这样吧,碰到我你们就直接喊我一声,或是看我一眼,好不好?”
依旧没有声音。但有一些孩子点头了。
孩子们真的长大了,他们懂得了包容、理解和尊重。
在以后的日子里,我教六年级数学,安老师依旧担任该班班主任,语数一肩挑。迎面碰上,我和孩子们会用眼睛打招呼的同时问候一声。如果孩子在前面,我从后面赶上,轻轻拍拍孩子的屁股或肩膀,依旧喊一声“闺女”或“儿子”,只不过声音小了许多。而孩子们从后面赶上我的时候,一般也要轻轻拍拍我的屁股或搂搂我的腰或拉扯一下我的胳膊。唉,我可爱、可敬的孩子们啊!
后来我调出了学校,到幼儿园做行政。离开学校时,经安老师同意,我特意到班上同孩子们告别,我展示了我们在一起获得的每一张奖状的复印件,包括班级的、我个人的、孩子们个人的,和每个孩子握手,向每个孩子说一句针对他自己特点的与众不同的祝福的话……
那是一场怎样艰难的分别,可能永世难忘!
转眼间孩子们小学毕业了,这期间,我和孩子们一直正常的走动着,虽然学校与幼儿园仅仅一墙之隔,但我经常收到孩子们寄给我的信件、贺卡,偶尔接到孩子们或家长打来的电话,或是他们的拜访。
有一天,我下班出幼儿园大门时已经是晚上六点半多了。嗬!只见41个孩子一个不少的站在大门外,原来,孩子们向我辞行来了。
他们簇拥着我走到学校门前看大红喜报上他们的名字:付钰、尹航、于洋、付潇然、王梦蛟、徐妍、梁曦,占据了全县前十名中的七位……
这时,聪明的淘气小子李方正忽然大声嚷着说:“同学们,我给柴老师提个问题,大家愿不愿意听?”我和孩子们都支棱着耳朵听,生怕漏掉了哪个字。
“老师,您过去一直都管我叫‘儿子’,我长得都跟您一样高了,您还敢叫吗?”
“那有什么不敢的?我一直都把你们看成我自己的闺女、儿子。”我抬高嗓门叫了一声“儿子”,只听得方正响亮地应了一声“哎”,大家“轰”的笑了。
谁知李方正又将了我一军:“您刚才叫我‘儿子’,我答应了;我叫您‘妈’,您敢答应吗?”
真是天真的孩子!“那有什么不敢的,你叫叫看?”方正高声叫“妈”,我高声答应“哎……”。
孩子们都跟着叫起来“妈 —!”……
啊,我的善良的、可爱的孩子们!
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……(文/河北省大厂县直第二幼儿园 柴东升 特约编辑/吴礼明)